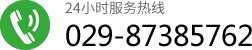耕地占補平衡政策是我國為了嚴格保護耕地、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而實施的一項重要土地管理政策。自實行以來,耕地占補平衡政策措施不斷改進,并在經濟建設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持續進行適應性調整與優化,有力支持了耕地保護目標實現。總體來看,這一政策經歷了從單一注重補充耕地數量到注重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保護、從單一注重耕地數量平衡到實行“數量為基礎、產能為核心”占補機制的轉變。
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嚴格落實耕地保護制度”“改革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作出明確部署要求。按照中央文件要求,自然資源部正在重點落實耕地占補平衡管理各項改革舉措。其中,耕地占補平衡將由“小占補”變為“大占補”,即將非農建設、造林種樹、種果種茶等各類占用耕地行為也統一納入耕地占補平衡管理。同時,實行“以補定占”,即“在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前提下,以省域內穩定利用耕地凈增加量作為下年度補充耕地指標和允許占用耕地規模的上限”。 “以補定占”重要原則的提出,反映出我國已實行20多年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正從“量出為入”向“量入為出”轉變。
耕地占補平衡中,耕地的占用可以視為“出”,耕地的補充可以相對應地視為“入”。耕地的“出”和“入”是矛盾的兩個方面。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矛盾普遍存在,推進工作就是把握矛盾、解決問題的過程。抓住主要矛盾促進工作落實,是唯物辯證法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們黨所倡導和堅持的科學工作方法。筆者認為,耕地占補平衡中“以補定占”的提出,反映出耕地“出”和“入”這一對矛盾的主從地位變化。
“量出為入”,關鍵在“出”,“出”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從11號文首次提出耕地占補平衡概念一直到“以補定占”原則提出之前,建設占用耕地(即“出”)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補充耕地(即“入”)的目的是為了達到耕地數量(質量、生態)的平衡,處于矛盾的從屬地位。例如,11號文出臺的背景是“一些地方亂占耕地、違法批地、浪費土地的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耕地面積銳減,土地資產流失”;28號文出臺的背景為“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圈占土地、亂占濫用耕地等問題尚未根本解決”。這一時期耕地占補平衡政策文件的出臺,是違法亂占耕地嚴重、耕地面積快速減少背景下的補救措施。補充耕地的要求也是與占用耕地相對應的“占一補一”“占優補優”“占水田補水田”等。雖然2009年國土資源部出臺《關于全面實行耕地先補后占有關問題的通知》后,建設用地報批必須做到“先行完成補充耕地,做到先補后占”,但“先補后占”屬操作性和程序性要求,此時的耕地占補平衡管理尚未在土地利用規劃和計劃等源頭環節對建設占用耕地作出先行性限制。因此,這一時期的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大體上符合“量出為入”的特點。
而“量入為出”的關鍵在“入”,“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以補定占”的核心內容是“以省域內穩定利用耕地凈增加量作為下年度補充耕地指標和允許占用耕地規模的上限”。即先保證耕地數量的增加,再談建設占用耕地的多少。補充耕地(即“入”)處于矛盾的主要地位,建設占用耕地(即“出”)只有在耕地增加的情況下才能獲得相應數量的占用指標,處于矛盾的從屬地位。耕地“入”和“出”主從地位的變化,也是我國當前面臨的耕地保護嚴峻形勢的客觀反映。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顯示,全國耕地面積19.18億畝,較“二調”減少1.13億畝。加之各級地方政府職能邊界的界定尚不清晰,耕地占用(即“出”)的數量指標難以合理估算,通過耕地增加(即“入”)數量來反向制約耕地占用將更為有效。因此,耕地占補平衡從“量出為入”走向“量入為出”,是我國當前耕地保護形勢下的邏輯必然。
實行耕地“量入為出”,進一步凸顯了耕地保護的紅線意識和底線思維,要求居安思危,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縱觀我國歷朝歷代,糧食充裕的時期,國家就容易實現穩定;相反,糧食生產如果出現問題,出現糧荒、饑餓,國家就容易出現社會動蕩。
面對當前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糧食多一點少一點是戰術問題,糧食安全是戰略問題。無農不穩,無糧則亂,這一幕在古今中外反復上演。一個國家只有立足糧食自給,才能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進而才能掌控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大局。我國耕地保護形勢依然嚴峻,守住耕地紅線的基礎尚不穩固,耕地“非糧化”“非農化”問題依然突出。勤儉節約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智慧。耕地保護大環境要求我們必須珍惜每一寸耕地資源,精打細算、“量入為出”地利用好每一塊耕地,堅決守住耕地保護紅線和糧食安全底線,以一域之穩為全局之安作出貢獻。